以「体制依附」看「国民性」,中国人的政治观念底色
「官本位」与「帝国本位」的社会生产机制
在讨论「国民性」的过程中,我觉得最显著的现象就是中国人强大的「体制依附」——公务员与教师资格考试的热情。这个现象相信不需要我进行介绍。当然你现在一定条件反射式的想到,中国的「体制依附」拥有经济解释和制度解释,这是一定的,就如上次我们所说,为一个现象进行某个视角的解释,是最简单的事情。
那中国显著的「体制依附」现象能够有何种视角?可能是我们理解「现代国民性」的关键钥匙。
一、全球「体制依附」综观
最值得做的事情不是跳入经济和制度分析,而是横向对比。对国家职位的热衷当然不是中国现象,但可能需要通过细致的对比,才能在表层的相似之下,发现细节的差异。
韩国的考公热与补习文化在中文社群也津津乐道,而孟加拉威权体制的倒台,导火索就是国家公务员职位针对军队子女分配特权,这说明「体制依附」不是中国的独有。从世界范围内来看,印度、印尼、巴西、土耳其、西班牙等国,都有「国考热」,这里面很多国家的招考比甚至远大于中国国考的平均86:1。
如果要证明中国人没什么不同,到这里就可以结束了。不过往细节看,全球「体制依附」有很大差别。关键就在差别里。这些国家里可以首先剔除欧洲左翼历史国家,这些国家中主要考公热是「全国教师」考试,有社民党背景的国家都有大规模公立教育体系,公立教育财政扩充导致教师岗位供给增加,从而导致教师报考人数增加,在西班牙招考比达到6.5:1,在青年失业率极高的意大利,这个比例到达17:1。当然中国这个数据非常恐怖,其实每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人数都大于国考+省考人数,报名规模从2016年的260万暴涨到2023年的1265万,其中2023年教师净增只有11.4万,招考比110:1,这当然也是「体制依附」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中印尼和巴西最近几年国考人数暴涨,甚至印尼到达396万报名人数,比中国还多。不过这两个国家都经历疫情前后国家财政的变化,尤其印尼此前遭遇财政困境长期冻结国家公职人员招聘,从2018年开始重启,招聘名额一下子全国就有23万人,当然激发了报名热情,但虽然绝对数量巨大,印尼的国考报名人数已经从2018和2019年的绝对高位稳定下滑,也就是对于人口大国印尼,虽然有国考重新放开,绝对热度持续了2-3年而已。
考公热情下降符合基本世界潮流,年轻人怎么会愿意投身无聊且上升图景缓慢的公职呢?这在与中国文化类似的韩国和台湾也是一样。虽然韩国考公热也是热点现象,但韩国考公人数在稳步下降中,招考比从2021年的35:1连降到24年的21:1,报考人数从高峰值31万人到2025年的13万人,四年来下降了一半。和中国文化最接近的国家台湾同样是如此下降趋势,台湾国考热情本来就不高,从2015–2024年参加「国家考试」中的公务人员考试报名人数由约32.8万降至16.6万。
各国考公人数都因其自身社会文化环境有一个基准值,这个值有高有低,但排除经济和招考制度的短期扰动,各国考公占人口比和招考比都在稳步下降。这里面有几个大趋势,公务体系薪资与社会差距拉大,各国公务人员福利逐渐透明化与社会持平,公务人员收入的随全球普遍财政困境的风险。
公允地讲,这些问题在中国全部存在,但在中国则完全是另一副景象。
二、被点燃的「强国身份感知」
我们可以拉长时间,考察中国「体制依附」现象,首先排除这20年的人口因素,中国80后生育高峰是1987年,此后进入一个缓慢的下滑过程,所以中国「体制依附」在08奥运后的增长,不可能有人口因素。
观察中国「体制依附」,有个很有趣的现象,中国是从人口生育高峰对应的例如2000年到2025年「体制依附」一直维持高位吗?完全不是,中国2005年国考报名人数31万人,计划招录8200人,招考比37:1,到2025年报名341万,计划招录3.9万,招考比86:1。省考也一样,从2013年的200多万人规模,到达2025年的530万人规模,教师资格统考起点2012年的17.2万人,到2023年的1265万人。所有「体制依附」项目都有非常恐怖的上涨。
而这些问题用经济决定论和制度决定论是很难解释的。以经济问题为例,如果经济问题是完整解释,那么应该观察到例如08金融危机和22年疫情危机后「体制依附」增加,而在此后经济恢复后报考热情就应该下降。这当然反应在了数据上,以国考为例,08金融危机后与22年危机后都有大幅攀升,但就算是2012年-2018年中国经济相对稳定时,国考人数几乎从未回落,而是进入平台期依然稳定上涨,在這10年國考招聘數沒有大漲,甚至2019年還大跌(这10年国考公务员报名人数从105万涨到143万,省考从250万到490万)。从经济上,中国国考有强烈韧性,体现出易上涨,难下跌的情况,这与其他国家的经济波动明显不同。
用制度决定论也难解释,实际上从2016年全面从严治党后,公务员工作已经退去了「事少清闲」的特征,现在大家基本知晓公务员面对大量监察和运动行政,工作强度极大,工资水平非常一般且近年还面对降薪欠薪压力。因为高强度从严治党,这份工作的风险也不小,过去大量的体制非正常特权和福利,也在「从严治党」下遭遇回退。基层作威作福也遭遇社会舆情监督(近年大量特权事件引爆网络倒逼国家入场)。从「制度性价比」上讲,很难认为从2005年-2025年,中国体制内公务员、省公务员、教师处在上升通道。
那为什么在这个情况下,中国人体现出与经济和制度变化无关的强大「体制依附」韧性?这才是与其他国家都完全不同的。这种韧性该如何解释呢?我相信诸位都知晓「上岸」概念,与中国社会广泛存在的「体制内外生殖隔离」以及「上岸第一剑,先斩意中人」的概念,以及体制内对外相亲的诸多乱象。我想这种「文化身份」是值得思考的。
中国年轻人对体制有强烈的「身份红利」与「情感红利」,虽然二者已经不具备经济和体制支撑。但拥有强烈的「文化支撑」,这样的支撑从05年到25年的20年间是逐渐增强的。因此可以说,中国年轻人和社会有强烈的「国家认同」和「国家本位」思想,而近20年的经济增长叙事,是强烈的「强国叙事」,进而「加入强国体制」不是一个经济制度理性思考,而是一种强烈的「身份感知」。
我想说的是,此种「身份感知」是近20年爆发性的「体制依赖」的根基,这份「身份感知」的基础共识,是「国家-社会」截然二分,是我在《疫年纪事》中提出的「真假国民」观念,是到2025年中国人依然相信,「体制内」是真正的国民,而体制外是「贱民」的强烈「帝国化身份敏感」,虽然这已经不能被经济和体制支撑了。
三、「真假国民」——「官本位」与「帝国本位」从日常到规范
这决不代表在05年前,中国人没有这种「真假国民」意识,但可以理解为在中国经济、国际地位没有树立,且受到早期互联网「公民社会」文化与意识的一代,这种官本位与国家本位的意识像是一种潜伏的病毒,没有跟随社会风气转变而爆发。其爆发就是奥运会、以及2010年代的「强国叙事」,彻底点燃了「体制依附」的身份与情感回报。这在其他国家,不管是印度印尼西班牙韩国台湾,都是不存在的。这是中国式「体制依附」的本质区别。
你应该为此感到惊讶,因为随着市场经济、互联网、居民财富、全球交流的发生,「官本位」处于绝对不利的位置。不管我们如何看待2012年后习近平任期的中国,但社会主轴依然是逐渐走向信息流通开放,经济思维提升的。在这个背景下,中国人反而被点燃「强国官本位」热情,这是一件奇怪的事,这与其他国家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有本质区别。今日全球右翼政治的民粹与民族主义,甚至带有「反官僚」的特征,认为「官僚」是全球化基础体系的一环,美国人对美国的热爱,不会转化为考取美国公务员的热情。这其中「帝国本位」与「官本位」的敏感,是一件在2025年颇令人惊讶的事情。
在这里我们一定要区分三种不同的「官本位」状态,中华传统帝国的「官本位」,改开前全能国家的「官本位」和当下中国「官本位」的区别。在传统中华帝国,你可以想象帝国与民间是泾渭分明的两个世界,传统帝国不具备现代社会毛细血管的能力和庞大的官僚体系。科举制塑造了「加入体制」的传统,这是从一个世界进入另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这种两个世界的框架在现代社会是不存在的,因而同样具有科举制传统的韩国和台湾,并不会延续这样的「体制依附」热情。
在改开前的全能国家,官员对社会拥有绝对掌控力,大到厂矿干部,小到大队主任,在这个时代,「帝国本位」和「官本位」完整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对每个人的命运具有实质性控制。在这个时代拥有某种「官本位」思想,就完全可以从经济和体制上进行理解。
但当下中国,虽然国家权力依然强大,但中国早已不是全能国家,市场经济和互联网对国家权力的冲击和实质性解构是非常明显的。不管如何抱怨当前中共对社会的压制和予取予求,实际上其掌控力与社会处于拉锯状态(到2025年中国传统公民社会完全歼灭下基于网络也可以发生江油事件)。
到这里我们可以复习福柯的《性史第一卷:认知意志》和《安全、领土、人口》,从改开前全能国家的「官本位」到当下的「官本位」,就是国家不只通过实际的控制,而是通过知识生产塑造「生命政治」的过程。而「生命政治」就是当前「国民性」的塑造和唤醒,是中国人潜伏的「帝国本位」病毒的激活。
这里面有几个点尤其值得思考:
「国民性」的「生产」而非「压抑」:很多人提到中国人的行为解释,将其单一解释为中共的高压和投下的恐惧。但这是真的吗?从2012年至今,中共为国人提供的只有恐惧和强压?而没有自豪?社会参与?如果没有,人民应该因为压抑和厌恶而远离体制,即便他们维持消极。但实际情况是,「国民性」并非压抑之物,而是具有强烈生产性,国民性生产新知识,产生新身份,塑造新的欲求。尤其在福柯的视野里,塑造正常/异常。即属于国家与体制是中国的正常(真国民),而属于外国与社会、商业的是异常(假国民)。这种社会意识塑造才是关键的。
「国民性」分布式唤起:正是因为「国民性」存在,而非单独「党意志」存在,中国的「官本位」不是自上而下靠国家意志塑造的。大多数人的父母都在强力推进「官本位」以及体制才是「正常」的意识。现代政治权力是去中心化的,中共也是如此。社会的个人节点,以及媒体,以及社会组织,都在共同推进官本位与帝国本位思想,这才是「国民性」的运作方式。
不是「惩罚」而是「规范化」:这才是福柯最后的真意,国家真正能力不靠惩罚,而是形成规范化社会过程,以「引导行为的行为」为术——让个体自我管理、自我审视,成为权力的合作者。中国人愿意接受「自我审查」,是「国民性」导致的只有体制才「正常」,反体制「异常」的思想根基。
四、「现实-精神-共识」混合体
到这里,基于「体制依附」背后的「现实-精神-共识」混合体概念,你应该有了更多的感受。「体制依附」当然有国家招考人数,福利体系等现实的一面,但与其他国家的对比来看,我们可以剥离经济决定论与制度决定论的成份,展开背后精神与共识的领域。
一窥中国人「官本位」与「帝国本位」在今天的独特生产机制,真正压抑社会的,正是这种知识与规范的分布式生产。而让中国在经济与互联网背景下,竟然「官本位」与「帝国本位」规范在社会中旺盛生产和繁殖的,正是根植于每个人心中的文化底层,即我们的——「国民性」。
你同样可以想象,以国家和体制为「正常」,以商业和社会为「异常」的中国人,在面对社会转型时,可能会带来何种抵触与强大的阻碍。
歡迎你在Patreon支持我的創作
我提供的全部知識與信息服務都是免費的,這之所以可能,是因為大家對我的支持,一月一杯咖啡或兩本書,支持我繼續不懈創作。
歡迎下載我全部知識與信息服務的清單:
我不僅有Substack,還有大量YouTube,書籍,播客,NewsLetter,社群,歡迎查看精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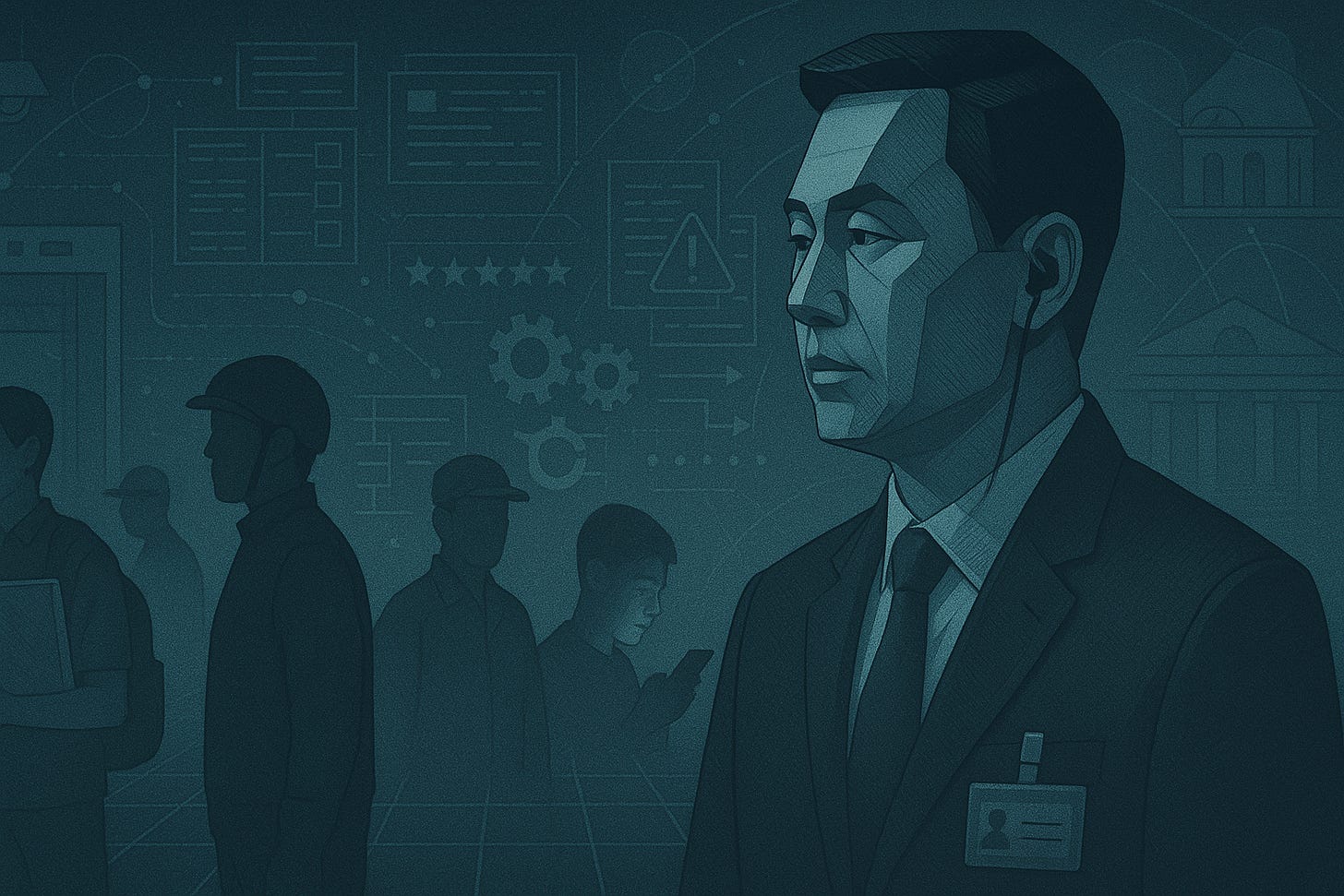
这让我想到在西方国家,身份认同更多来自职业、社区、兴趣、宗教等多元领域;而在中国,因为社会极度原子化,并且一切能让人产生身份认同的组织都依附在党国之下,因而在很多人眼里进入体制才是最终极的身份象征。不恰当的比喻,就像很多人玩游戏时要把装备买到顶配为止,不然就觉得低人一等或满足感没那么强烈。
看了几篇,整体行文杂乱,数据和观点没有整理:比如考公,招考比和总人数数据对比混杂,缺乏分类。不知道是不是真如直播所说,是20-30分钟写出来的文章。这样杂乱的行文做podcast的文稿没问题,因为听众状态本就相对随性,写作文章可读性则不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