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清中國轉型重要的「國民性」問題,與經濟制度決定論的貧瘠
為何五四百年後,還值得討論「國民性」問題
最近三個水槍手的節目,題目是《中國人是否值得救》,除了中國人的倫理責任外,探討的是「中國人能不能救」的問題,這個問題當然指向「國民性」的經典五四命題。
很多人拒絕「國民性」問題,認為這個問題涉嫌種族主義,誠然在「國民性」問題探討之初即五四時期,正值「社會達爾文主義」高漲,彼時的討論有強烈「種族主義」色彩,這種討論的風格對今天有影響。不過「國民性」當然不必綁定於「種族主義」,我也拒絕姨學帶有種族主義色彩的探討方式。但如果忽略這個問題背後的「傳統」、「風俗」、「文化」對社會進程和轉型的影響,卻可能錯過最關鍵的問題。
例如中國威權傳統對中國人在「總統制」與「議會制」接受度和選擇中的問題。例如中國人的體制依附性在未來對民粹主義政治的轉移問題。例如中國長期的民主、NGO、公民社會汙名化對未來公民社會信任度的問題。甚至中國古典「黃老」的政治虛無主義對未來轉型中困境和挫折的問題。
這樣的話題幾乎可以無限列舉下去,其中有的很關鍵,有的與制度和經濟重合度高,有的帶來政治挑戰卻並不根本上阻礙政治議程,有的甚至不一定是中國特有現象。因此「國民性」問題是一個問題意識的考驗,不僅對社會理解至關重要,也拷問著對中國未來關注者的思想水準。
一、國民性問題的三段論
為了展開這個問題,可以簡述關於「國民性」問題思考的三段論。第一個命題當然是「作為種族主義與達爾文主義的國民性問題」。這個問題簡單來說可以上溯至啟蒙運動時期,啟蒙運動逆轉了政治學的「德性中心主義」,開始尋求基於理性和物質的「本質答案」。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中的「地理決定論」,即寒冷氣候養成勤奮性格,適合共和制;熱帶氣候導致懶惰,適合專制。這是最典型的「國民性」與政治制度的決定假說,這種論點的20世紀精緻版本就是「大陸文明」與「海洋」文明之辯(我相信很多反對「國民性」的人接受兩文明二分法,說明這個問題存在一定的深度,認知失調的人大有人在)。
隨後是對「國民性」拒斥的「經濟決定論」與「制度決定論」。前者代表是馬克思,與大家朗朗上口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我想國人輕易接受反「國民性」的「經濟決定論」,雖然很多人嘴上操著哈耶克(哈耶克肯定不是經濟決定論者)的話語,其實內心奠基的是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的弔詭在於,建基於「歷史唯物主義」的「經濟決定論」卻發明出了「階級史觀」的另類「種族主義」,其高峰就是《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文章,兜兜轉轉還是回到了某種「思想劣根性」,只不過不以國民劃分,而以階級劃分。
馬克思是個非常蹩腳的二流思想家,但其觀念歷經近百年共和國史匯入中國人的思想底層,塑造了某種這篇文章語境下的「國民性」。
當然「經濟決定論」與「制度決定論」有更切題的版本,就是「制度經濟學」,以近幾年最火的Acemoglu–Johnson–Robinson思路為線索,基本論證了制度是「一階原因」。即便文化、傳統等要素存在,制度依然是最根本原因。我很大程度上認可這個觀點。但認可這個觀點不是討論的終結,這恰恰是展現問題意識的時刻。
即便制度是「一階原因」,那麼對於「制度變革」這個問題呢?中國從共產極權走向開放社會的過程中,在「共產極權」作為既有「一階原因」的前提下,主宰和推動這個轉變之「動力學」的過程中,文化、傳統等要素扮演什麼作用呢?
到這裡,就是國民性問題的第三命題了,是真正重要的命題。
二、制度決定論的貧瘠與「國民性」的需要
首先,問題之解釋與問題之解決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事情,這是很多人忽略的。一個人例如因為長期飲食習慣導致肥胖症與三高,問題的解釋是病理學的,用全套生理病理解釋,可以回答他為何出現現在的問題。但如果要解決他的問題,則馬上進入生活習慣、收入、觀念的問題。
同樣,對中國人的任何行為和社會現象,都可以找到一個「經濟決定論」或「制度決定論」的解釋,稀缺程度啊,共產黨極權的強度啊等等的,作為成熟的社科思考者,炮製解釋從來是最簡單的事情,上述問題炮製一個「文化決定論」視角的解釋也不會困難。但如果要面對這個問題的解決,而不是解釋,真正的問題就不在「制度決定論」了。
我嘗試提出一些問題:
中國當前就是沒有新聞自由,沒有制度化輿論監督,但基於互聯網的輿情非常洶涌,也事實上起到了監督作用。但互聯網輿情的監督,在動機、觸發點等問題上有什麼樣的特徵?哪些問題更容易產生民間自發參與和監督?這個問題對中國的當下重要嗎?你覺得這個問題的答案更接近中國人經濟上如何匱乏,社會公共品服務供給如何欠缺?還是中國人對「平等」問題以及「官民關係」的某種「傳統性情」呢?
共產黨政府從來沒有改革嗎?從80年代經濟與政治改革,到最近的「民營經濟座談會」等,政府持續釋放中央威權監督下的社會實用性務實改革。不論其信用、真誠性、效果。中國人對務實的現實主義微調具有極高的接受能力,國家甚至可以把「提供持續可感的現實主義微調」當作一種新的統治術,在中國矛盾高發的週期成為平息民怨的方式。如果要影響社會對於這個過程的輿論導向,這是不是一個需要考慮「社會習俗」的問題呢?
當然與「提供持續可感的現實主義微調」相關的,還有「提供持續可感的的反腐與官員問責」。當然這不是中國的特有情況,「反腐」在全世界極右翼政治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如果深入細節,「中式反腐」與其他國家的政黨政治中的腐敗指控還是又相當大的區別,也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以及所謂的「底層」問題,在傳統的「經濟決定論」背景下,所謂「底層」總是被看作沒有政治德性與政治能力的人群,只能被「擺佈」和「利用」。要麼就是「階級決定論」下,「底層」才是社會進步的中堅力量。怎麼看待這兩個幾乎完全相反的主題?如果你要引導一場選戰,你對所謂「底層」的策略是什麼?這也是一個複雜的話題,例如對2024年美國大選,就有「經濟決定論」的很多版本解釋,和以《家鄉裡的異鄉人》(Strangers in Their Own Land)為代表的文化解釋的區分。
制度決定論描述一國的政治與社會的宏觀現狀,當然是絕對的「一階原因」,但當我們描述變遷,描述未來政治與社會變革時,「制度決定論」就變得貧瘠了。
三、「精神是一塊骨頭」
這個問題當然還有更深的意謂,到這裡我都可以拋棄「制度決定論」作為「一階原因」。就是黑格爾的「精神是一塊骨頭」,這句話有截然相反的兩個意謂。
黑格爾在生涯早期一度沉迷「顱相學」,這在當時的德國非常流行,算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一種極端樣式,即通過觀察頭骨可以判斷一個人的犯罪傾向等特徵。隨後黑格爾認為,顱相學是理性發展的一個特定階段,具體位於「理性」章節的「觀察理性」部分之下,標題為「觀察自意識與其直接現實的關係」。
在這個視角下,「制度決定論」依然是「觀察理性」,是「顱相學」式的社會科學。把活的人的行為與觀念世界讀成「硬的物質」,且不必說制度本身就是一個「精神客體」。
所以我們可以明白,不存在「總統制」或「議會制」,不存在「民主」或「專制」,這不過就是一個個的「概念」和「詞彙」。也不存在一部成文憲法的印刷紙張,不存在一根特警的甩棍,不存在網信辦的電腦和機房。
不管是有形的制度實體,還是制度的概念,還是制度構造的人際博弈與經濟關係,將其真正「實體化」的,是與人們的習慣、傳統、理解黏合成的這個「現實-精神-共識」混合體。這算是現象學的基本視角,在現象學的視角下,這「現實-精神-共識」混合體才是「一階原因」。而「制度決定論」不過是「觀察理性」的某種過度簡化。
問題到這裡,當然就變得複雜了,也對思考者提出了極高的要求,對於太多在簡要馬主義和短視頻薰陶下的人,這已然超出了其世界複雜度和思考的上限,但其中所有概念又對其展開了任意理解的空間。誰說這種社會的「現實-精神-共識」混合體,不在不斷刷新塑造著新的「國民性」呢?
而轉型的過程,就是與這個「國民性」角力與共存的過程,克服與改變這塊「精神之骨」。
(這只是「國民性」問題的第一篇文章,還會繼續與大家探討)
歡迎你在Patreon支持我的創作
我提供的全部知識與信息服務都是免費的,這之所以可能,是因為大家對我的支持,一月一杯咖啡或兩本書,支持我繼續不懈創作。
歡迎下載我全部知識與信息服務的清單:
我不僅有Substack,還有大量YouTube,書籍,播客,NewsLetter,社群,歡迎查看精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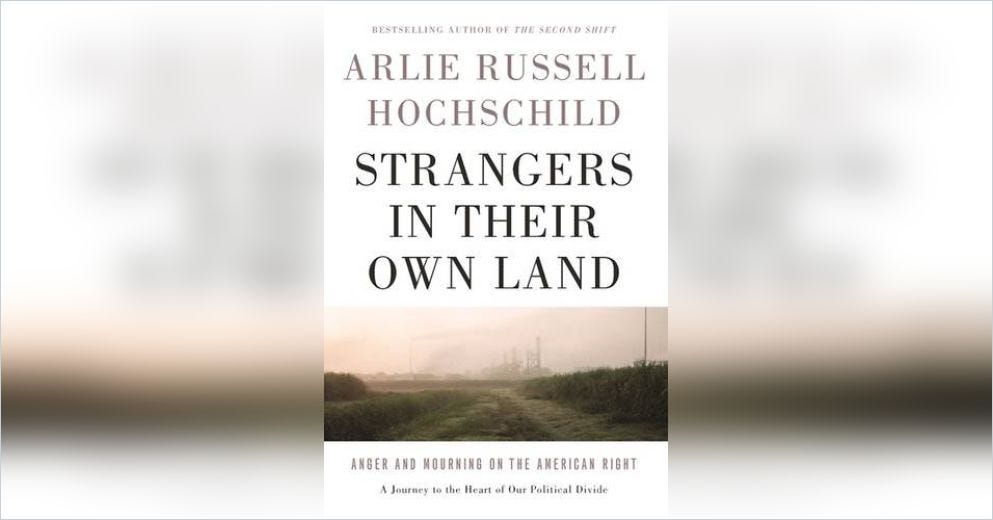
感谢小李老师提供的宝贵视角,昨天看了节目,也看了discord的一些讨论,还是看这篇文章收获来得大。尤其是最后一段,让我看到了走出制度这个“一阶”原因的可能,很有启发,感谢!
为什么是国民性,而非社会观念或者主流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