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制度经济决定论”,最难的不是智商与知识
到底如何告別,真的是個很難的問題
最近关于「国民性」的讨论,让我发现「制度决定论」已经成为了自由派的思想底色,很多问题下面,都能发现简洁而振聋发聩的:
「是制度问题」,就像一句咒语,他代表的不是讨论的开始,而是讨论的终结。「是制度问题」,还需要多解释什么吗?
切忌把Acemoglu–Johnson–Robinson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理解为「制度决定论」。「制度经济学」的问题意识是解释国家间繁荣与财富差异的问题,反对另外的「决定论」思想,如Jared Diamond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为代表的地理决定论,Max Weber的「新教伦理」为代表的文化决定论。因为全世界有如此多民主国家,他们为何有穷有富,看上去繁荣与制度无关。三位的思想是应对这个问题意识。
事实上,他们非常关注文化影响,如果你感兴趣可以阅读2024年Acemoglu与Robinson的文章《CULTURE, INSTITUTIONS AND SOCIAL EQUILIBRIA:A FRAMEWORK》,里面的观点恰恰是文化与制度、经济同为人们决策的「工具箱」,且具有高度主动与流动性,会形成一个「博弈均衡」。在这个视角下,你就把「国民性」当作中国文化传统在给定社会条件下形成的「均衡态」就好。在这篇论文中,恰恰分析了儒家文化在中國大陸與台灣分別支持威權與民主體制,具體闡釋了同一文化集合如何產生截然不同的文化「均衡态」。
「国民性」与「制度」都不是单一充分要素,当然,这句话是绝对正确的废话。一到具体分析问题,就不是这么回事了。
(這是「國民性」討論的第三篇文章,可以先閱讀第一篇和第二篇)
一、“制度决定论”是初级反思
首先我想提示的是,一定要对「制度决定论」和「经济决定论」不满足。诚然,这二者都是机制分析(mechanism analytical freamwork),不是市井人士依靠「直觉」的判断,具有一定的技术性,容易产生分析和思维的快感,从而生出一种高明之感。
但就如我一再指出,对社科而言,炮制一个分析性解释是最简单的事情,为一个社会现象找到一个表浅的制度解释或经济解释,其实没有比「直觉」前进多少。
我能理解制度决定论的一种情感结构,尤其是在制度作为最大问题的中国,「制度变换」是「中国问题」的根本药方,当然如此。所以在制度转换期,将社会问题解释为「制度问题」,有助于唤醒民众的「制度感觉」,证明司法独立、竞争性政治、分权监督的重要性。我的整本《疫年纪事》就是这样的一个分析,问题意识恰恰是反对共产党的「道德决定论」,认为中共是魔鬼和愚蠢,才会有2022年的荒唐,而将复杂的社会现象形成一个多面的制度解释,但落实在最后部分「中国人的自由观念谱系」,也就不是制度问题了。
「制度解释」是一种符合中国当下情况的好用「工具」,对于社会大众的中国「善恶报应」伦理直觉,当然前进了有意义的一小步,但如果你满足于这一小步是「社会本质」,那就真的大错特错了。况且绝大多数人连这一小步都没有跨出去,命题:
中国人不勇敢,是因为共产党的压迫太严密和恐怖
这是一个成熟的「制度解释」吗?当然不是,但这恐怕就是绝大多数人「制度决定论」的观念水平,或者台湾大罢免乱象,是「极化政治」云云。到这种程度的解释,到底和「直觉」有多大区别呢?「制度决定论」与「经济决定论」的视角素养,大概仅仅是初中程度。
二、“制度决定论”的悖论和情感结构
既然如此初级,那么「制度决定论」为何在自由派如何广泛和持存,答案当然不是大家傻,而是这是一种强烈的「情感需要」。我们上面已经接触到了一种情感——一种超出庶民「伦理直觉」的分析性优越。
第二重更深的情感结构要再次回到「制度决定论」的悖论。既然制度有强大决定性,那么中国作为千年帝制,百年专制制度浸淫的国家,如何能摆脱这个制度呢?诚然,中国现在的一切问题都可以炮制一个制度解释,但这个解释如何导向最关键问题——中国该如何获得新制度?制度决定文化与意识,那么中国的改变当然被制度「锁死」。
你会发现到这里,问题基本卡住,所以「中国崩溃论」和「美国干涉论」才如此盛行。「制度决定论」恰恰反对很多人嘴里浪漫的「自救论」,既然制度和经济决定中国人的心灵,那这么强大的制度,谁还会「自救」呢?那么绝大多数人的消极政治状态,恰恰涌现为中国无法自主改变。所以未来的希望才是「制度自我崩溃」和日本式的「外来制度强加」。
「制度决定论」有浓浓的悲观色彩,但在悲观中其实得到了真正的情感抒发。如果你问一个人,如果你持有「制度决定论」,那中国岂不是没有内生制度改变的可能了?因为绝大多数国人都被中共极权制度所「决定」?我想答案多半是:对啊,但那又不是我的责任。
「制度决定论」是大写的免责声明,不仅如此其反过来成为了一声民族主义号角,Youtube大有网红鼓吹「中华民族优越论」,认为中国人聪明、勤劳、现在中国的问题,都是共产党的制度害的,如果不是共产党的制度,中国一定会成为极端强大的国家。这「制度决定论」兜兜转转,竟然与中共的「百年复兴」殊途同归。
「制度决定论」在即便追求自由人之中的流行,恐怕这种「个人免责」与「民族主义」才是其中重要的情感需求。
当然「制度」作为第一因的答案不是悲观的,「二次改开」正是《自由的窄廊》中关于「制度漂移」的实际例证和可能性,这进一步证明了舆论中的「制度决定论」是个多么简化的版本。
三、讨论问题的尺度
问一个简单的问题,为何现在持有自由思想的中国人,不像其他中国人一样被中共的制度「决定」呢?当然也可以炮制出一套制度和经济的解释啊,大城市啊,特定年代啊云云。那这么说,每个人都没有自由意志了?自由派之所以是自由派,建制派之所以是建制派,在出生的那一刻就已注定。我写下这篇文章,你看到这篇文章以及产生的感受,自宇宙大爆炸那一刻就已经成为宇宙的命运?
这当然是扯淡。回到个体尺度问题,很多人依然相信道德判断的重量,不然为何这么多人爱谈「自救」呢?贩夫走卒也能成为热爱自由的人,中共干部也能弃暗投明,三代被党迫害,喝多少洋墨水,也能自由地成为党的走狗。但既然人人自由,自由的人集合涌现的「集体秩序」,是如何被制度和经济决定的呢?这里面是概率和统计问题。这也是「一人一杀」的无力感,对一个个人我用尽全力,对结构问题我无能为力。
个体的自由,集体的特征,黏合这两个问题尺度的,恰恰是一边放弃极端道德自主(高尚者的自救),一边放弃集体的必然(制度经济决定论),而将个体的决策看作一种多策略的博弈。因此我极端排斥个体抉择的「短期利益」决定论,我们今天为一切行为解释和辩护(考公、买股票、入党、成为大白etc.),都是短期利益决定论和一句「这符合经济理性」。当然我也排斥项飙和齐泽克式对个体快感和理解的沉溺,精神世界需要制度和经济构成基本的博弈结构。
因此能够黏合个体自由意志与集体可预测框架两种尺度的,是尊重主体能动情况下,意识到任何社会经验和利益背景下,与主体理解间可能出现的断裂,就算是股票投资这样看似纯粹“利益”的行为,背后也是「生活世界中的意义—理解—协调」的完整关系。世界上不存在纯恐惧、纯快感、纯利益可以用于决定人的行为。政治经济中都存有文化斗争的色彩。
但难度来了,「现象学」思路不是一个简单的分析框架,更不是一个可以半个小时熟练掌握和运用的东西,并不像「制度决定论」和「经济决定论」可有有极端简化的解释。
四、“制度决定论”的浪漫主义
最近一两周,我看了大量以「制度决定论」包装的反智言论和自以为是。其中一条说:
以前专门做节目区分浪漫主义的基于文化的旧德国式国家建构和法国式的基于文明和理念的国家建构,现在自己走到自己的反面。
认为「国民性」分析是「浪漫主义」。其实这是我停止做翻电2.0的一个原因,我恐怕我输出的内容简化为教条,维特根斯坦简化为:我不喜欢的话就是「语法问题」和「语言空转」。反对「浪漫主义」和「心理学意识形态」等于人的精神不存在。我也很犹豫要不要把「现象学」更明白的呈现,甚至犹豫要不要多谈福柯的“生命政治”,唯恐谈完了一切社会规范都变成了国家阴谋。如果任何思路都会劣化为极端简化模式并被教条使用,谈论这些的意义是什么呢?
尼采在《历史的使用与误用》中,提出“历史主义”的命题,其核心是指出现代人罹患的「历史病」,将对过去的分析和崇拜超出自身生命需要,使历史摇身变成审判当下的“法庭”。这才是浪漫主义历史观的根基,在这个意义上,「制度决定论」听上去是工科文化“理性客观”的阐释,但其和「工业党」一样,不过是一种历史主义的浪漫主义。我说这个不是想报复那个指责我「浪漫主义」的读者,把这个帽子扣回给他。
而是想说明,反对「浪漫主义」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浪漫主义」从启蒙理性的反面中蹦出来,抓住的就是个人强烈的情感需要,其中最深的,就是哪些伪装成不是情感的情感,伪装成常识的谬见,伪装成民生问题的意识形态,伪装成科学主义的极端怀疑论。
如何逃离这种浪漫主义,为何尼采诉诸「强力意志」,为何我对「现象学」如此踟蹰。就是此种心灵需要尼采所言的「适度遗忘与勇于开端」的气质,将一切不理解为必然产物而是「权力、情感与诠释的缠结的结果」,放弃一劳永逸的合法性,为新的价值与新的形式开路。
这里需要的不是智商,而是决断与强大的心灵。一个平庸的平民时代最缺乏的东西,因为在平民时代,根本不需要什么决断与心灵,只需要一句轻飘飘的话:
想搞纳粹那套就直说,哪用这么多废话
当说理不再,智识委身于网络输赢,这种新的,简化的「生命意义」将随煽动与挑逗将人的思想侵蚀殆尽。这问题复杂极了,文化斗争既然是现象学意义上生命理解的根基,为何「网络输赢」却不是呢?凭什么我想到的「文化斗争」就比「网络输赢」更高级?就琢磨吧。
歡迎你在Patreon支持我的創作
我提供的全部知識與信息服務都是免費的,這之所以可能,是因為大家對我的支持,一月一杯咖啡或兩本書,支持我繼續不懈創作。
歡迎下載我全部知識與信息服務的清單:
我不僅有Substack,還有大量YouTube,書籍,播客,NewsLetter,社群,歡迎查看精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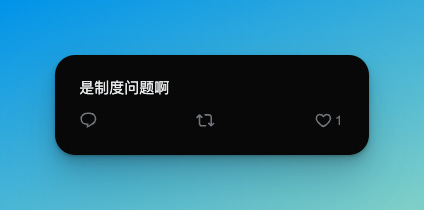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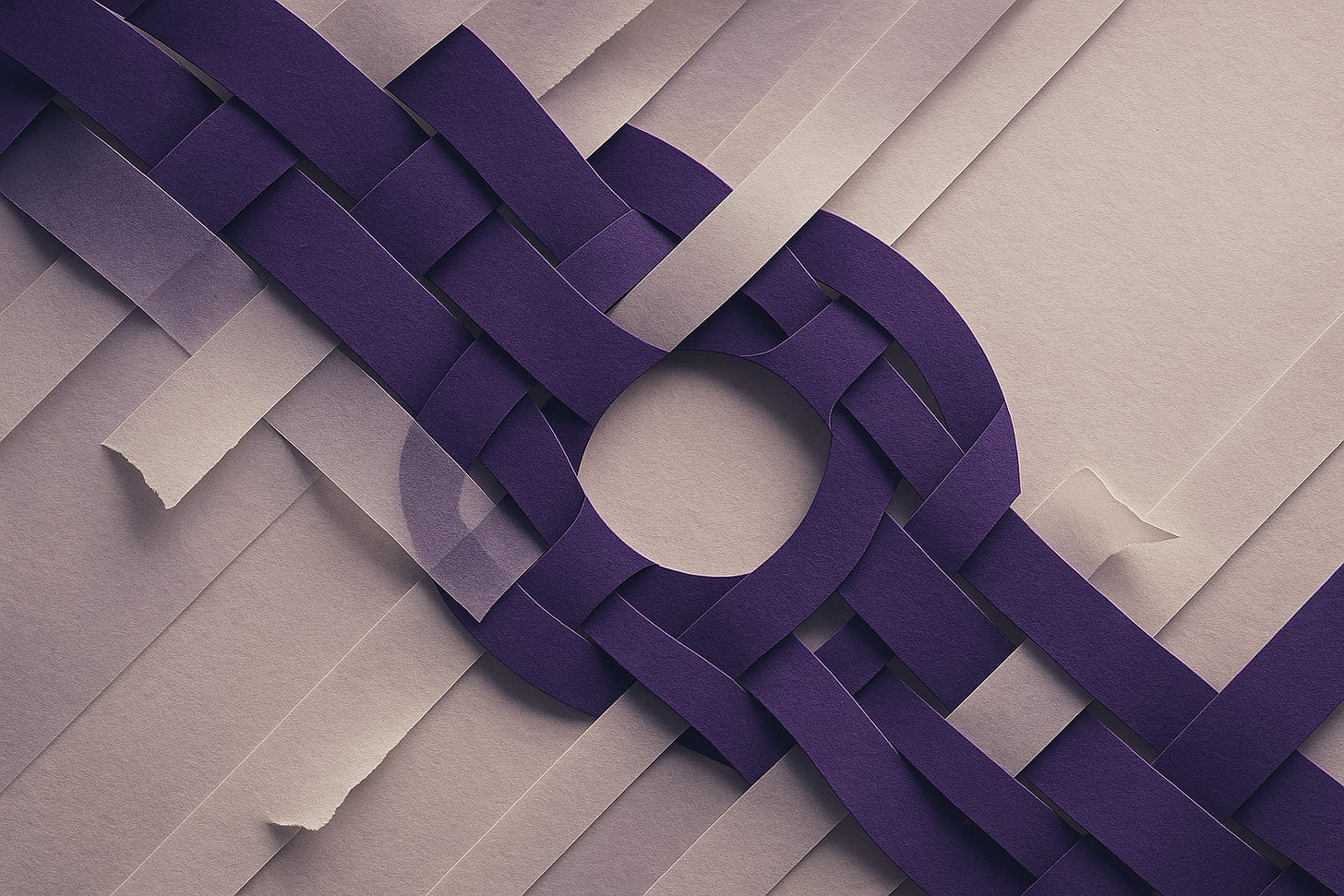
目前最支持的一集。一个现象到底是什么决定的还得具体看这件事是什么,中国的情况从宏观上来说自然是制度决定论能作为最有利也最符合自由派感情需要的叙事. 但是如果说制度是唯一的决定要素是不充分的解释. 当具体到家庭问题,男女问题,教育问题时,我相信制度之外的文化要素会成为更主要的决定因素(当然这绝不意味着制度不发挥作用,作为一个前全能国家制度在间接地影响所有领域). 在这些比较微观的领域里,中国的传统儒家传统,专制帝国传统我认为在塑造伦理体系方面比共产极权本身的文化影响更大。有趣的是,这三者本身都构建了一种强大的集体主义文化,而市场经济和自由主义的传入也输入了个人主义文化. 这种个人集体的文化张力哪怕是制度改变我认为依旧是一种持久的角力过程. 就好像日本与美国,欧洲各国在民族性上的体现并不是简单的制度决定论造成的,民主制度并没有与日本长期的集体主义文化形成不可调和的矛盾. 地理决定论在中国的很多社会事件我认为没那么能解释问题. 枪炮,细菌与钢铁所说的地理决定论能够解释那些前殖民国家比如新几内亚和西方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差距,是地理本身限制了新几内亚人的发展. 同时,物种缺失也能解释新大陆的原住民和旧大陆的差距. 用富饶理论和资源诅咒也能去解释那些石油国家之类的资源国家发展上的落后,但这些是比较长期的过程,中国现代社会是经历了短期多次根本性的重塑,地理决定论可能能解释历史上的专制帝国怎么形成,但是很难解释人口高速流动的社会的一些共通问题。对某一种决定论的笃信确实是一种浪漫主义,但是我觉得在可能也是惯性,一种单一因果关系的惯性. 普通人很容易产生一种只要存在A,B就能形成了,但是实际上B的形成A只是必要条件,但是还存在C,D,E的作为补充. 还有就是公共说理下想要的充分性解说在实际社会动员时可能反而削弱动员力,要让人动员起来反对某个东西我认为举出个受众能认可的主要理由在执行上和信息传播上可能是一种更好的技巧,这个主要理由甚至不需要是制度,可以是更简单的赚钱逻辑.
这一篇我最喜欢,这种直接面对质疑以及直白的剖析确实最有力量,这种直截了当的告诉你别躲在文绉绉的词句装清醒,里边只有浅薄。对我这种老听众算是当头喝棒。支持!